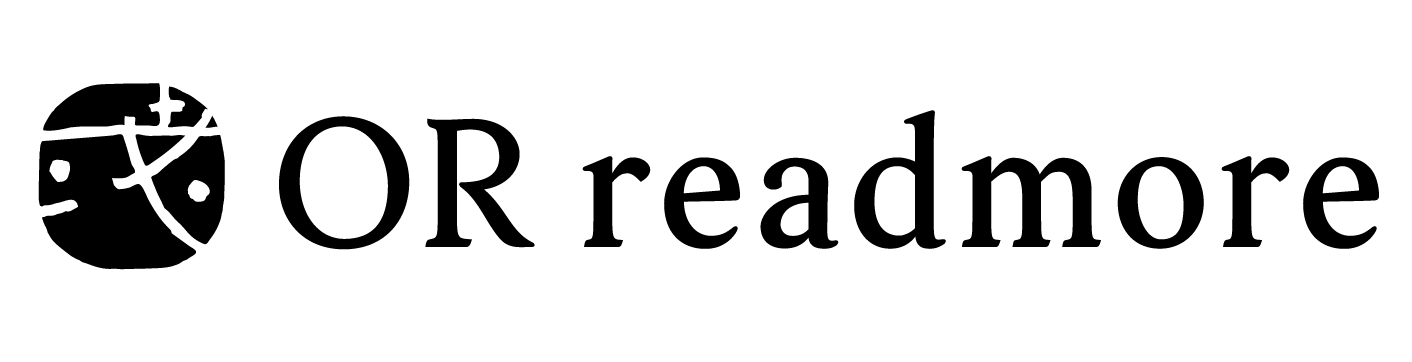1997年,陳果的《香港製造》拍攝「偏差少年」的故事,弱智的阿龍在街上撿到陌生女子阿珊跳樓的血跡遺書,從此男主角「中秋」被阿珊的鬼魂糾纏,他說這叫性騷擾,因為他會在夜裏夢到阿珊之後劇烈冒汗驚醒,原來是清洗夢遺後的內褲。故事設定看似戲謔,但中秋同時也跟備受欺負的阿龍、絕症女孩阿屏一起汲汲營營尋找阿珊的遺書收信人,並替阿珊的情傷抱不平,甚至到墳場大喊阿珊的名字,而那素樸的友誼與正義,使墳場這樣帶有死亡氣息的場所,仿若野餐郊遊般開心,成為全片最明亮開闊的一景。
2021年,任俠、林森這部無法在香港本地上映的《少年》裡,男主角阿南也是夜晚冒大汗,但是清晨驚醒之後,看見是鏡中後背被警棍打得傷痕累累。阿南驚醒之時,也是女主角YY的自殺意念落成書信之時;同樣年輕的YY,是曾在街上被撤退的阿南給撞倒而被警察逮捕的手足。所以,阿南跟其他香港人一起奮力營救想要自殺的YY,在水泥叢林之中,靠著機遇及巧合找到人。跳樓的那刻,天台及巷戰奮鬥的手足,都在一幅象徵性的畫面上,伸出了多隻援手,成為絕望寫實之中(這部片不時穿插真實的抗爭影像)最有力度的一則影像主張。

社會要如何把年輕人逼上絕路,年輕人又會如何回應這個社會?《香港製造》給了一個複雜且有層次的答案,帶來煙霧瀰漫的惆嗆味道;《少年》則給了一個簡單無比的答案,鏡頭幾乎只近距離地跟在人身上,其餘以真實影像便足夠說明。我城的現實已無需更多詮釋,電影裡少年的能動性,要回頭引導這社會。這個意識具體呼應了《時代革命》裡的那句「不是時代選中了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也是《少年》作為運動當下拼搏拍出的劇情長片,以劇本及表演將人們看不見的事情「演出來」,因而具備無可取代的作品價值。
過去的香港電影,不乏飽富正義且面貌多元的警察,而今無論在現實或電影裡,我們的記憶深刻著鎮壓抗爭的殘暴黑警。正如《少年》裡演出警察家庭的十五歲少年,被社工問到會否擔心在「發夢」(抗爭)時遇到父母,他說「最好遇到被打死,反正『黑警死全家』」這樣簡單的一幕,台詞精確而無須贅述,警察的社會意義已經定型,政權亦無容得異質樣貌的空間。不只是警察形象的質變,少年的形象也在轉變。《香港製造》裡中秋原本要拿刀向「包二奶」的父親咎責,卻在廁所撞見另一名制服少年砍了他父親,原來那父親長期性侵制服少年的妹妹,中秋感嘆「原來不是只有我,每個人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極權之下,少年們各自被訴說的故事也趨向雷同,因為需要直面暴力、刑期及生命威脅這樣更具張力的「情節」,家庭及親密關係也多少會與政治意圖掛勾而產生掙扎,彼此能共感認同;而比起過往的討債復仇、逞兇鬥狠,勇武疊磚及拋擲汽油彈才是當代少年的行動,鬥爭的對象從有權有勢的敵方,變成一整個政權。
電影敘事中的正反雙方、正義與不義,都有著更截然的表現。若將作品並置,而非以單一的角度去認識這些角色,我們將看見創作者置於其時空,作品本是對整個社會景況的回應。
從「死亡」的主題出發,《香港製造》裡一開頭阿珊便跳樓了,中秋在飽受挫折之後,發現阿龍被老大殺死,阿屏沒有等到他的捐腎也因病死去,中秋說他要做「驚天動地」的事,便是槍殺老大,最終在阿屏的墳墓旁自殺。《少年》一開始是YY在手機畫面之中,興奮從高樓自拍看繁榮的彌敦道,好似普通無憂慮的小孩;然而她也得知香港少年因抗爭的無力感而墜樓,她帶著鮮花致意,自己上街被捕後,則感到人生希望渺茫,決定走上絕路。電影最後,朋友向天台邊的YY喊話「香港是不會因為你一人的死而改變的」,她則落淚點點頭,淡淡說了句「我知。」便轉過身。
對不同世代的年輕人而言,殘酷及絕望的本質並沒有消逝,誰也都想從這場恐怖的災難中免疫,可是現在有更多的少年起身行動,不願只是長大並妥協,就抹滅了理想。反送中少年們的「驚天動地」,是如水般綿延數月的抗爭,逼得政權醜態盡出,為歷史寫下一頁,是集體而切切實實的驚天動地了。

而「救命」這樣的主題,也是屬於反送中運動的特徵,無論是「以死明志」、「更激烈的手段來喚醒」或者「攬炒」意志,正如同香港主權的命運,在高度貧富不均及生活條件侷促的競爭社會裡,多數年輕人前途也未明,充滿躁動及焦慮。《少年》的台詞經常精確點到香港在地的脈絡,就像阿南對即將前往英國讀書的女友說「你是中大畢業,不像我考不上大學,香港留給我們這些沒有選擇的人就好」,這樣的設定也快速凸顯出階級的衝突。YY的父親長年在中國工作而未返家,被警署逮捕後,律師也告訴YY等這班年輕人的法律代價及出境的風險。看不見「離城」選擇的香港少年,更可能不得不挺身為爭取自由而付出,甚至不惜犧牲。「要走,還是要留」的命題從現實之中的七一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行動裡被警察封鎖而絕望的情境,延展到大抓捕及國安法之下的移民潮,人們或許無法翻體制,卻仍能夠努力拉住那些想要以個人生命「想走」的手足。

因為時間,不一定總是站在少年的這邊,少年只能天真地期盼自己不要長大,如英文片名《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電影裡,角色的相遇是在2019年7月21日,YY說那天人們開始在街上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少年》的片長只有《時代革命》的一半,如其片名,它處理的可能是一個局部,可能「通俗簡單」,在大歷史當前顯得小了,但它會碰到很純粹的情感核心,尤其是年輕人的核心。也許過了十年二十年,《少年》才會因為未來的觀眾「幾乎分不清哪些片段是用真實影像,哪些是特別拍的」而驚嘆,或者因為它把紀錄片不可能拍到的警署內畫面、受強暴者的慟言、黑警小孩的掙扎、路人老人也拿著手機在街上救人的畫面等等也被「演」出來,才受到肯定。期盼這部電影,能像我們曾經在電視上看過的輪播經典港片那樣,少年對抗黑警的故事會被傳唱,決不無疾而終的勇氣,也會再鼓舞下一代的少年。

延伸閱讀:
2021金馬影展 │ 傳承「香港製造」的精神──訪問《少年》導演任俠
翻閱香港電影,見證半世紀以來的中港政治關係史──《幻魅都市》
Ma, K. W., and C. H. Ng. “普普香港: 閱讀香港普及文化 2000~ 2010 (一)[Pop Hong Kong: Reading Hong Kong popular culture, 2000–2010 (1)].”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