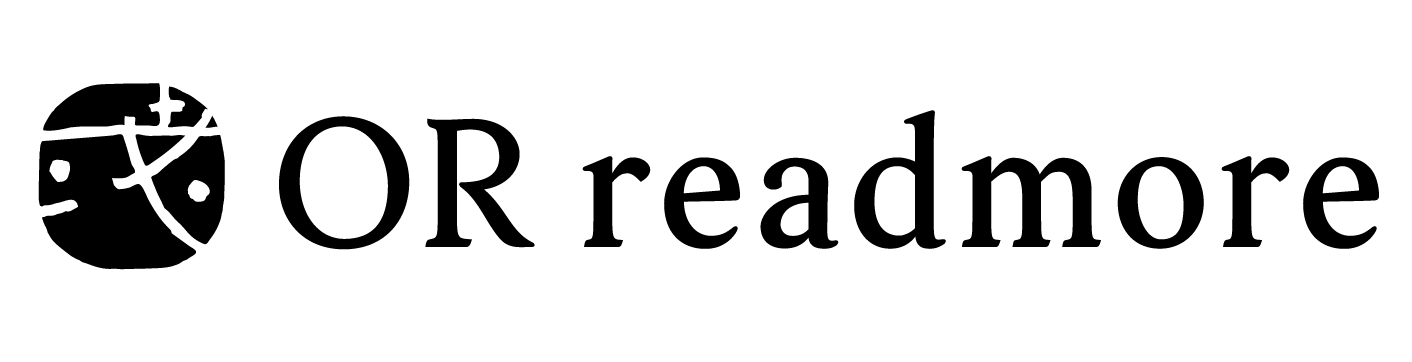現實複雜多面,需要多重觀點交會之處,政治宣傳總簡化為正邪交戰懶人包。但現實中從無完美的英雄。
一九八七年的紀錄片《怒祭戰友魂》描述六十二歲的二戰老兵奧崎謙三,因為在新幾內亞兩名士兵同袍死亡,調查四十年前的真相,有人說是因逃兵被處決,有人說是因為吃原住民屍體而遭處決。原來日軍戰末斷糧吃人,上級下令「黑豬」(原住民)可以吃、「白豬」(白人士兵)不能吃。奧崎謙三逼軍官供出,因為原住民跑得快、抓不到,所以殺士兵來吃。結尾奧崎謙三要槍殺下令的士官,重傷他人,被判勞動十二年。
奧崎謙三是個荷索式的暴走怪咖,電影一開頭就處處令人瞠目結舌:他開店的鐵捲門、平日開的宣傳車上都大字漆著「殺死前首相田中角榮」;他主婚致詞和字卡介紹自己殺過一個房仲、用小鋼珠射擊裕仁天皇、散發淫穢傳單侮辱天皇等,坐牢十三年九個月。然而,紀錄片拍完四十多年後,導演原一男在《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一書訪談中說:
奧崎謙三是商人,精於掌握利害得失,憤怒時都經過算計,知道怎麼生氣能討好觀眾。(假)
奧崎謙三決不是一個有邏輯思考的人,經常誤判、貿然行動。全片前半部奧崎謙三有兩次發怒揍人,是詮釋真實的自己。後半奧崎謙三脅迫古清水中隊長,是真心想殺了他。因為古清水想掩蓋他殺了上等兵吉澤徹之助,所以奧崎謙三才會痛毆古清水,讓他放棄掩蓋。(真)
奧崎謙三這類的算計多到數不清。(假)
這些與拍攝無關,純粹是他獨特的生存之道。(真)
正因為他意識到鏡頭,才刻意放大這些特質吧。(假)



所以,原一男想說什麼?一段話換了四次車道、左右蛇行,吞吞吐吐說不出口,知道全球觀眾奉奧崎謙三為真漢子;其實可能是戲劇型人格,渴望引人注目,活在自戀的偉大神話裡,戰爭食人罪行給了他當英雄的舞台。《怒祭戰友魂》四十四年來經典地位建立在一個戲精上,原一男不能說,卻又衝動說出來。每說一句戳爆國王的新衣,就打圓場挽回。然後再戳,繼續打圓場。上網搜尋報導,《鏡週刊》報導原一男來台參加影展,也挖苦奧崎謙三像網紅一樣饞鏡頭:
奧崎謙三用彈弓射小鋼珠攻擊天皇不中也沒人發現,情急大喊「攻擊天皇」才終於引起注意被捕。
奧崎抗議教科書粉飾侵略,叮囑導演原一男:「我要開車撞教育部長,畫面一定要拍到。」
右翼團體參拜靖國神社時,他要花束藏刀混入人群亂砍:「畫面一定要拍到。」
完全表演藝術。片中,奧崎向戰友說:「我靠著抵抗生存下來。」拍片一如他的身體,是抵抗的工具。美國導演麥可.摩爾的紀錄片《華氏911》、《資本愛情故事》、《科倫拜校園事件》延續了奧崎謙三直搗黃龍的訪問風格,透過被警察、警衛推擠阻擋,堵麥逼問要人、逮住他們吃了誠實豆沙包的瞬間,來暴露權力的專制。
另一方面奧崎謙三的表演欲,很像《殺人一舉》的五戒青年團領袖安華,年輕時是戲院黃牛,得以免費看好萊塢電影,迷戀約翰‧韋恩等英雄殺人的帥氣;演出紀錄片,也想滿足好萊塢電影夢。《怒祭戰友魂》的焦點是戰爭罪行,而書中原一男的訪談將戰爭罪行變成背景,焦點轉到質問奧崎謙三是否物化了戰爭罪行,將權力絕對的邪惡變成舞台道具襯托他。事情是這樣的嗎?
觀眾判斷戰爭傷害士兵的程度時,會參考受害者的反應。如果奧崎謙三沒那麼憤怒,卻表演出他所沒有的憤怒,這是陳述虛假不實。但我重看《怒祭戰友魂》,老兵說,日本已經投降了,軍營被兩萬人包圍,上級卻命令他們戰死為止,換做外國軍隊早就投降,不可能弄到吃人。片中呈現將領濫權之慘烈,我認為奧崎謙三再怎麼戲精都合理。我們習慣了消防隊、警察、軍隊、醫師強制成員付出代價執行任務;但奧崎謙三等個人自發付出坐牢等代價去抗爭,我們卻質疑他別有用心。這種思考只是極權抹黑異議者的話術。
《鏡週刊》報導原一男自述經常煽動被攝者:《再見CP》裡他叫腦麻者裸體坐在馬路中央;《日本國VS泉南石綿村》,石綿受害者十幾年來溫和抗爭,原一男挑釁:「你們就只能做到這樣嗎?」亦即如果對象不像奧崎謙三這麼暴衝,那麼原一男負責暴衝。溫馴的石綿受害者既想衝,又受成規束縛,內心矛盾成為被攝者與原一男的拉鋸。而原一男內心暴衝和常規的矛盾,卻成了奧崎謙三和原一男的矛盾。如果奧崎謙三是在表演,那麼拍他算是真實嗎?原一男這樣的自我質疑,肯定沒有停止過。

想必有人會輕描淡寫說,原一男受訪嘲諷奧崎謙三,只是演講搞笑炒熱氣氛、順便打破造神而已,並無不敬。我認為原一男就是忍不住每次要去戳破奧崎謙三,說明原一男的攻擊性,並不亞於奧崎謙三。如果他沒拍片,說不定就是整天碎碎念的公務員,對妻兒任何事都要挑剔一番,嘴巴太毒搞到沒人要理他。欺負兒女是把攻擊性轉移宣洩在最不會反抗的對象身上,而拍《怒祭戰友魂》是奧崎謙三、原一男去攻擊不能惹的最大黑道──政府。
全書歌頌紀錄片的政治貢獻,視為游擊英雄,但到了後半段,藤岡朝子卻反對期待紀錄片發揮政治宣傳功能、立刻改變人心。她說所謂電影,不應該是功能主義,非得對什麼有幫助才有價值。電影的價值因人而異,假如只剩下宣傳社會問題的價值,豈不是非常單調無聊?
她甚至還沒提到用情節、影像表達見解,結構、音樂、剪接、掌握氣氛的準確等,光是政治題材就惹毛她了。我在想為什麼這本書很少提紀錄片的劇情和藝術表現,同時也在想究竟哪部紀錄片對她而言,會「只剩下宣傳社會問題的價值」,會不會《殺人一舉》對她都十分單調無聊?
她避提成品,只舉例《不丹少年轉大人》原本落選的提案「女孩踢足球後改變人生」,指責此案充滿美國夢,拍女孩跨性別只是趕流行、政治粉愛看而已。她說若照原案拍,或許就變成刻板毫無創見的電影。所幸落選後再次提案、改拍女孩的哥哥,「令人驚喜」、「描繪了出乎意料的人生之美」。做人遇到阻礙更應活出自我,拍片面對現實不如人意,努力打破框架和僵局,這樣電影才有趣。
我覺得跨性別如陳世襄評《天龍八部》說的八個字「無人不冤、有情皆孽」,往往一輩子都辛苦,頂多逆勢前進,不會是一舉完滿修成正果的美國夢。要了解她讚揚《不丹少年轉大人》「令人驚喜」、「描繪了出乎意料的人生之美」時,究竟在說什麼,讀者除了自己去看片以外沒可能猜到。
而我即使去看了都猜不到。《不丹少年轉大人》全片老爸喋喋不休「我不是逼你,但你若不出家繼承我們家寺院,寺院和財產都會被政府和別人奪走」,十幾歲兒子痛苦無奈。妹妹則勸他別當喇嘛持五戒守貞,該戀愛享受青春,兄妹睡前就是湊著手機分享最新鄰里正妹照片。我是不懂,既然老爸結婚生子也繼承寺院了,為何強求兒子要守貞才能繼承。既然要守貞,那兒子不生兒子,將來寺院照樣拱手讓人,早晚的事,其實沒差不是嗎。
該片沒再往下挖老爸偏執的原因,只是理所當然接受專制。日本觀眾可能從中看到一個傳統、忍耐、父權的日本家庭,媽媽逼想當男孩的女兒穿粉紅色,爸爸逼一心學彈吉他唱情歌把妹的兒子出家,兒女挫敗苦悶,曠野荒涼不毛,以宗教道德訓誨代替文化,老小踢足球是唯一娛樂。少年向學徒打聽僧侶訓練,得知要每天四點半起床早課,大驚問能上網嗎,答下課可以。他喃喃安慰自己「至少還能上網」,籠中鳥的命運令觀眾悲從中來。
不知該片令藤岡朝子「驚喜」、「出乎意料」、「打破框架」在哪,又為何咬定電影拍跨性別必然刻板?她是想罵某些政治紀錄片陳腔濫調卻不敢直言;還是拒看殘酷壓迫、只想關起門來歲月靜好?她不說,只說跨性別勵志題材拍不出創見。
再上網讀林木材〈專訪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東京事務局局長藤岡朝子〉一文,該年她策畫山形影展的日臺紀錄片單元,所以請她評論臺灣紀錄片,起初她猛打太極拳:「這幾年我沒看太多臺灣的紀錄片,所以我無權回答,你問Makiko或其他人。」「我知道的不多。」
然後她辯解:「要說年輕世代沒有趣的作品很容易,但並非如此簡單。有世代斷層,因為我認識吳乙峰、全景,還有他早期的學生,我想知道他們有沒有繼續。如果年輕的電影工作者說吳乙峰作品不夠好,我要做點別的,好東西就會誕生,或想我如何和吳乙峰有所不同。因為吳乙峰強勢,就像小川紳介,佐藤真怕這樣的力量,所以他遠離並試著做出不一樣的東西,思考如何與眾不同,發展獨有的想法,強壯和夠堅定,是可以克服、打敗前輩的。」
本書跟她這段話給我相同的感受:似乎日本人不講壞話,除了歌頌紀錄片工作者,其他事情都在雲裡霧裡、模糊不清,閱讀必須不停上網調查每件事。藤岡朝子是隻躲在牆洞裡避戰的家鼠,迎空探出鬍鬚試風向,小心翼翼維護人際和諧。如果記者沒像林木材耐心等她把真話孵出來,就不會知道她從牆角也將一切盡收眼底。她怎會沒看太多臺灣的紀錄片,只是嫌品質不好,她既不想昧著良心說好,就算殺了她也挖不出她一個字說不好。她看片只能判斷不好,無法一一去問導演為何拍不好。其實也不用她告訴臺灣讀者原因,問她就是要知道她覺得哪裡不好而已。但為了閃避這個不好,她寧可堅持非體諒臺灣拍片苦衷不能評價。她這點倒是很像臺灣作品:一觸及加害者,馬上體諒起對方種種苦衷,堅持自己不知情沒有資格評斷,懸崖勒馬不敢踩雷,作品也就成了垃圾。
由發言可知,她認為臺片拍不好是因為,都在模仿吳乙峰的套路。我想那些片不是吳乙峰體,而是訴求堅強樂觀,既安全又催淚的臺灣體。《生命》沒有加害者,觀眾會想,地震天災哪有加害者,能怪誰?而不是想到災後重建工程標案、建築安全法規背後有多少政治問題。
書中說到導演松井至,曾為NHK拍紀錄片,訪聽障者回憶三一一震災時的避難實況。製作人宣稱觀眾習慣看片有聲音,要求導演為片中的手語配音。導演駁斥「觀眾必須耐得住沉默無聲的世界,才能明白那一天發生的真實情況」。最後勉強妥協,替手語上字幕。下次再受NHK審查壓迫,他就與人獨立策畫了紀錄片影展。
在此,本書的寫法兩次誤導讀者以為製作人爭取「要有聲音」,看到後面才知道爭點是「要翻譯手語」。導演要觀眾看不懂受訪者手語在說什麼,體驗聽障者聽不見震災廣播的困惑,同理其恐慌,這是亞陶的殘酷劇場。而製作人知道,電視觀眾不會乖乖坐著受「看不懂」壓迫,只會轉台。
這就像南韓導演鄭潤錫拍攝紀錄片《龐克海盜地獄首爾!》記錄輾核樂團(特色為厚重的吉他失真、低音、高速的節奏、blastbeat與令人費解的咆哮或高頻尖叫)「栗島海盜」,片頭註明「本片音量不均,忽大忽小,是為了表現社會不平等」。比起劇情片在幕後精巧繁複設計以展現情感,松井至、鄭潤錫想法可謂簡單粗暴。
松井至不翻譯手語,要用靜默讓聽人體會失聰。顯然來自1993年德瑞克.賈曼導演的《藍》,全程整個銀幕只有同一藍色,讓人體會導演失明感受。又如1952年美國前衛作曲家約翰.凱奇《4分33秒》的全程靜默,留白要聽眾主動幻想填滿。
松井至說,覺得手語十分美麗,想原樣靜默呈現於觀眾眼前。
鄭潤錫說「栗島海盜」表演聽來雖只是噪音,歌詞卻覺詩意,想用紀錄片翻譯那份詩意。
兩人都捕捉到感官的「美」,與拍攝題材第一眼墜入情網的瞬間。那個瞬間既召喚導演衝動去靠近、探索,也意謂必須保持距離、限制理解,在神秘中容許那份唯美盡情呼吸,投射幻想。當一見鍾情的內分泌激動過了,美在近距下暴露出實屬誤會,一夜醒來枕邊打呼磨牙的傢伙判若兩人,就像奧崎謙三在原一男面前的精刮算計與猴急,那麼原一男也須有勇氣承認自己的幻滅。不應在訪談幕後花絮中,而是以電影本身探索。理解原本不理解的醜陋,精神的「美」即悄然而至。
書中,鄭潤錫說,原一男在其劇本集上,手寫了一句話「人類極神祕」。
鄭潤錫崇拜原一男,看不懂日語,卻在神保町舊書店買了原一男劇本集,只因店員說是導演親簽版。讀者恍然大悟,鄭潤錫拍的栗島海盜,就是奧崎謙三那樣的狂人。鄭潤錫在找那樣的人,幼稚自戀,別人壓抑怕洩露的算計、狂妄與憤怒,他們無畏地翻出來裸露、自嘲。栗島海盜的鼓手權容晚是中產大學生版本,比奧崎謙三更自覺,人我折衝更世故熟練。片中演唱會,他一面挑釁聽眾「你們討厭我們的音樂,因為你們的品味爛掉了」,一面自嘲「因為我們更爛,所以我們喜歡」噗哧解消衝突緊張。
別人的內心話,是他們的表面偽裝。製造預期、打破預期,操縱落差,社交手腕游刃有餘。別人的內心算計卻是他們的表面偽裝,作為主角,他在全片中都與電影觀眾保持社交距離2.5公尺,從未卸下來回嘲諷的社交武裝讓人窺見內心。
我認為不是人類神祕,而是原一男只受那份神祕吸引。因為他不了解自己,所以陌生的拍攝題材,看來就像在前世相遇過那樣,命中注定、無可解釋。
吸引鄭潤錫的,是看不懂的日語,是栗島海盜噪音般刺耳快速、令人聽不懂的歌詞。即使讀到歌詞,還是令人搞不懂的幽默。〈金日成萬歲〉歌詞在副歌不斷嘶吼「金日成萬歲」之間,只穿插說北韓獨裁者金日成換了房仲業務等多少日常工作,觀眾看了也不知道歌詞在說啥。後來鼓手到警局作筆錄,說「聽眾乍聽歌名會嚇一跳,聽到歌詞才知道只是和金日成姓名同音的普通人。我有許多朋友就因姓名與金日成同音而飽受困擾」,觀眾才懂笑點在諧音梗。
這個結界,很像諧星曾博恩、老K「炎上」、「火烤」系列脫口秀,充斥外人聽不懂的內哽、邏輯迂迴隱諱,觀眾不懂仇女好笑在哪。而粉絲會笑,是因為感覺報復了權威,又受理解的結界保護,而感到安全。這是一群一點就著的人,說不出他們心存反抗時想懟的是誰。

書中鄭潤錫說,因為在大學專攻美術,記者常問他是藝術家還是電影人。紀錄片從業者則問他,他是拍藝術電影,還是搞社運。他覺得他同時擁有這些身分,抗拒別人貼他單一標籤。可能因為有了身分就有創作倫理要遵守、有生涯聖杯要追求,這些他都怕。
片中鼓手也說,不簽唱片公司,因為怕創作受限。明明渴望吸引眾人,但又害怕受控制而失去自我,全力捍衛孤獨。在叫囂表面下,那份孤獨、不安的心悸抖顫,召喚了鄭潤錫。
本書歌頌栗島海盜為對抗政府、爭取言論自由的鬥士。我認為他們對抗自己、爭取言論限制的成分大。
記者若問栗島海盜是搞樂團還是搞社運,應該是賞臉還肯問本人,其實觀眾不可能誤會。本書把他們寫成爭取言論的鬥士,證據是該樂團製作人朴正根轉發北韓政府推特,寫「請金正恩將軍給我們巧克力」(諧擬佔領區貧童向美軍要巧克力,諷刺南韓政府對美卑躬屈膝),被告為匪宣傳違反國家安全法。他向警方辯稱只是開玩笑,結果被判緩刑不用關。鼓手亦向鏡頭坦承對北韓一無所知,也沒接觸過統派。
鼓手自述創作思路,做搖滾就要找爭議激怒主流,才會令聽眾印象深刻。其邏輯無異網紅挑戰吃屎拼流量,既然北韓就是南韓最大禁忌,那就模仿北韓。作詞作曲,是從北韓政府推特發布的宣傳影片找MV素材,由一本《社運用語集》中取樣,拼湊出「北傀降旨:保障勞動三權」這樣的歌詞。令人錯愕,北韓比南韓更不可能保障勞動權。但鼓手說,南韓是尿,北韓是屎,都自稱民主,但都沒有言論自由。
顯然因為北韓和勞權都在南韓的對立面,所以把北韓和勞權扯在一起才成立,這種邏輯只存在於他的幻想世界,無涉現實。對他來說北韓不存在,金日成只是虛構的動漫喜劇人物。社運從大學高學費、拆遷、高房價等抗爭出發;栗島海盜卻是模仿社運用語,等於模仿北韓腔調、模仿龐克樂風。嘴巴講的不是心裡所想的,歌詞只是舞臺道具之一。栗島海盜沒有實質內容,你討厭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給你看,將自身化為南韓威權社會的顛倒鏡像。
就連劇情片《寄生上流》也會讓地面南韓家庭的鏡像--地下室的一家人模仿北韓,丈夫學軍隊呼口號感謝領袖(屋主),妻子學北韓央視主播李春姬播報,隱喻南北韓骨子裡是一路貨。這種批判在外人看來,只是《全民大悶鍋》的政客模仿秀,就酸民隨便嘴兩句的程度,膚淺而無內容,所以也沒殺傷力。栗島海盜亦然。
美與詩意,是不懂和共通體質的混合,召喚共通的觀眾共鳴。鄭潤錫感到栗島海盜神秘不可解,因其靠著模仿搖滾外觀,逃避實質,徘徊於自身困境門外,不得其門而入。空洞就是他們的魅力。
正如不是政府頒獎榮耀你就認證你第一名,也不是政府抓你就認證你激進,國安惡法只是樂團中樂透,一抓成名天下知。該片的價值,不是拍栗島海盜衝組以卵擊石證明政府專制,而是拍到中產子女「沒有理由的反叛」。正如支持北韓不是栗島海盜要捍衛的自由,支持勞權也不是。那什麼才是?
為什麼他們不捍衛他們所要的那種自由?
片中栗島海盜受訪,在嘲諷、自嘲間,不時互望、爆笑。其實房間裡沒事可笑,只是假裝輕鬆,掩飾緊張。像是在咖啡館裡對話,為掩飾不知所措而頻頻喝水。他們一直試著hold住,紀錄片享用了他們撐起來的表面,而不去理會那握拳手心虛汗的hold。也許他們習慣hold住,也許導演的態度就是要他們hold住,而他們感覺得到。為什麼非hold住不可,那才是權力向他們施展暴力專制之處。

本書是一個社會企業,有志推廣紀錄片文化,為介紹一眾紀錄片導演、策展人、發行商、資金鏈所作的群英傳。因而把這部紀錄片浪漫化為政治抗爭,讓理念夾帶作品傳出去。佔到了道德制高點,錯過了生而為人珍貴的不誠實。栗島海盜因而保持了神秘,在英雄星座的夜空中繼續閃爍。即使你是一個反英雄,仍會有人把你推上英雄寶座。
本書不談技藝細節,可能因為書名《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就已暗示歐巴馬競選口號的那種史詩壯觀、一擊斃命的英雄式「改變」,而不是日復一日的幕後底層勞動、產業沉痾。估計選片的範圍是山形影展和其他影展的得獎作品,記者也心存表揚要來封聖,而不是平等理解。
彷彿書的背面,有一本《一事無成的紀錄片工作者們》或《想改變世界但……的紀錄片工作者們》,等著我翻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