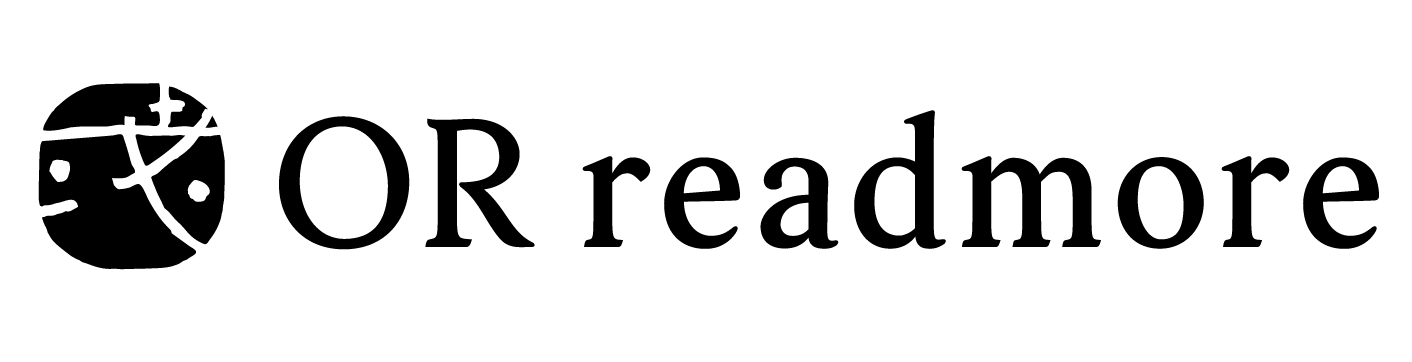《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編著團隊SOMEONE’S GARDEN,是由津留崎麻子與西村大助兩位兼具藝術、影像與雜誌背景的文化從業者共同創立,主要從事雜誌、書籍的編輯、設計、app、影像製作、活動舉辦等業務。在這次的企畫中,他們極富野心地圍繞著「GAME-CHANGING DOCUMENTARISM」這一核心概念,深入訪談超過30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紀錄片導演與相關工作者,透過反覆的探問嘗試重新定義紀錄片,捕捉紀錄片的全新意義。
這本書像一把石灰,倒進名為讀者的那杯靜水,頓時便泡沫翻滾、發煙起浪。
新聞報導台語金曲歌后詹雅雯自幼家貧,她是長女,十四歲到洗衣廠做工,從早上八點做到晚上,再去讀夜校,累到趴在地上睡著。她不懂為何爸爸從不跟她說一句「辛苦了」,直到二O一四年喉嚨長瘤、二O一八年唾液腺整個塞住無法分泌唾液、二O二O年五十四歲時因為當年洗衣廠接觸漂白劑、硫磺,毒物殘留而罹患帕金生氏症,左腦中度萎縮,爆瘦八公斤,爸爸才抱著她說「我讓你太歹命」。
原來爸爸不是不愛她,她落淚說「一切都值得了」。她感謝小時候爸爸買吉他教小孩唱歌,她把第一首學會的歌《為伊走千里》送給爸爸。二O一八年詹雅雯直播宣布罹病,透露有段時間鬱悶,鎖骨刺青「唵嘛呢叭咪吽」提醒自己「我是一個很正向的人」,每天起床對鏡合掌謝謝身體:「人生每個病痛都是有原因的,在提醒自己要愛自己的身體,應該把速度慢下來了。」
感恩、溫馨。
《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首篇訪談,便記錄了丹麥導演約書亞.歐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最初得知一九六五年大屠殺的故事。當時印尼一處大農場女工普遍得肝病,四十五歲就早早過世,因為噴農藥沒有防護衣、面罩。蘇哈托政權結束後,工人才敢爭取防護裝備。業主是比利時公司,不但昧著良心不給,還僱五戒青年團打人,工人只好放棄訴求。二OO一年,十年二十七歲的導演和同伴去拍攝工會抗爭者,發現女工都很怕輪到自己得肝病死掉。他問,沒防護裝備你會死,為何放棄訴求?
工人說,一九六五年印尼剿共,五戒青年團殺了很多人。工人們的家人不是共黨,只是工會,就被殺了,所以工人們怕被殺。現在還是同一批人當權,所以沒人敢碰這個話題。
在臺灣,大眾看到詹雅雯發病,記者、觀眾沒人問:一九八O年那間洗衣廠有過多少工人,四十年後她們還好嗎?
過年我回農村探親,親戚聊起附近多年來怪病頻傳、兒童過敏,傳聞是洗衣廠排廢汙染水源、土壤。但都是私下議論,無人會打破鄰里和諧去公開質疑、調查證實。
有多少工廠沒做防護隔離、沒做汙水淨化,為什麼知道有毒的人有權不阻止毒害?我們不會意識到「是你個人的問題」以外的可能。這種反應並不是偶然,是長久鎮壓的沉默餘震。
後來導演再回印尼北蘇門答臘,跟拍殺人者《殺人一舉》,然後拍了遺族《沉默一瞬》。
剿共時的青年團員們,至今仍驕傲炫耀殺人喝血、開膛破肚,從共黨手中救了國家。導演請他們重演殺人現場,拍了四十個人,都很自豪殺人,只有民兵領袖安華不同。安華帶他去頂樓,表演用鐵絲把人勒斃,講完突然開始跳恰恰。
讓人想起,韓國導演奉俊昊《非常母親》開頭和結尾同一場戲:母親為掩蓋兒子殺人,匆忙將目擊者滅口。事後意識到自己殺了人這件事無可挽回,她回應痛苦的方式,是在日落草原上獨自疲憊搖擺、扭動肩膀跳舞。
導演回憶《殺人一舉》的拍攝,初見安華,是去他家邀訪拍片,預計會被拒絕,但沒有。那天安華太太在客廳聚會,安華只好帶導演上頂樓聊天,說已經四十年沒爬樓梯。一上頂樓,安華說:「這裡有很多鬼,因為很多人在這裡被殺。」
「我試著用好音樂、跳舞來忘記這些,讓自己開心。喝點酒、嗑大麻、搖頭丸,喝醉了感覺像飛起來。你看,我的舞跳得還不賴吧。」每當入睡,殺人回憶就會變成噩夢,安華睡得很不好,後悔斬人首級沒替他闔上眼睛,才會夢見自己被斬首。但不願看精神醫生,他說因為「看精神醫生代表我瘋了」。
將記憶封印沉睡的,不只是安華,而是整個國家,等著一部紀錄片來喚醒。
《殺人一舉》片中,青年團員受訪,談起當初政府動員各校中小學生去戲院看一部描繪共黨殘酷的電影,給小孩子留下創傷,但有助於殺共產黨。青年團員說這電影讓他殺人沒那麼罪惡感。而記者說,電影中共黨殺人放火的劇情,其實是自己亂編的,只求達到效果就好。看似青年團員殺人無數,其實這部政令片殺人無數。
這段情節不言而喻告訴觀眾,為何要有紀錄片、為何紀錄片要挑戰當權、為何導演不拍本國反而跑去第三世界「消費苦難」?因為多數人的世界觀就是政令片塑造的。如果紀錄片不去抵抗,恐懼就能世襲,印尼農場女工們就不敢再抗爭要求防護裝備,將來還會一代又一代繼續死於農藥毒害。
訪談中導演自述,當他把電影成品給安華試看時,先讓劇組赴機場待命,防備安華若看了不高興要殺人,立刻飛去外國避禍。超過數千萬印尼人看過《殺人一舉》和《沉默一瞬》,發現政府和軍隊的腐敗濫權,導演已被印尼列黑名單禁止入境。換成印尼導演拍,就算本人流亡,想必連親友都會受害。顯見外國紀錄片以獨立地位,介入印尼當權者與人民潛在的衝突,填補了真相的懸缺。又如書中提到,無國界醫生組織於巴黎成立,是因為在現場治療還無法救人,必須把政府鎮壓平民的暴行告訴全世界。二O一五年阿富汗美軍轟炸無國界醫生醫院,造成四十二死,美國、阿富汗都不准外界調查,是無國界醫生組織拍紀錄片報導了此事。

醜聞弊案吸引大眾目光,也是權力所欲掩蓋的。二O一七年日本森友學園欲設立「安倍晉三紀念小學」,籌備期間由安倍晉三妻子出任名譽校長,以1.34億日元向政府購得價值14.23億日元的校地。曝光後,交易取消,財務省理財局、近畿財務局等交出文件,檢察官電腦鑑識卻查出已刪除文件涉及官員的部分,結果近畿財務局負責該案的男職員在家自殺。Netflix日劇《新聞記者》取材此案,相形日本各大電視台不敢捋虎鬚,外商資金撐腰才能拍。
菲律賓導演拉夫.狄亞茲以自幼戒嚴鎮壓、外商勾結政府掠奪土地回憶,拍攝《驕陽逼近》、《悲傷秘密的搖籃曲》、《惡魔的季節》探討暴政,回應杜特蒂新的暴政。菲律賓強拆貧民窟、射殺居民來蓋鐵路的黑歷史《巡警生涯》,是由菲律賓文化中心的獨立電影資金,贊助菲律賓導演傑特.雷伊可拍攝。在轉型正義之路上,菲律賓紀錄片已跨出大步。
除了透過影像工作者之口挖掘紀錄片的意義,編著團隊也將目光聚焦在日本、台灣、加拿大、荷蘭等世界各地的紀錄片影展和推廣者身上,嘗試呈現這些活動的動機、效果,以及他們各自因地而異的處境,企圖以此延伸紀錄片關於「改變」的戰線。
本書採訪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策展人林木材,他直言臺灣沒有紀錄片產業,本地紀錄片一年僅上映十部,缺乏電視、電影產業資金,只能靠政府補助,無法執行龐大計畫或跨國合拍,在世界各國看來極為異常。日本記者沒有追問「為什麼臺灣沒有紀錄片產業」、「為什麼影視產業資金不給紀錄片」,但我想知道。
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籌設者之一藤岡朝子,說明山形影展的交流氣氛,舉例許菱窈台片《小金剛》以強烈影像風格,把弟弟車禍身亡的過去,拍成一部有如散文隨筆的短片。影展映後座談時,日本女性觀眾提問:「我非常明白你失去弟弟的悲傷,但本片何不更強烈呼籲駕駛小心開車?」藤岡從中看出了文化差異:臺灣導演追求藝術表現,日本觀眾則是合理主義。
這位臺灣導演想搞藝術、觀眾要求政治探索,不只在山形影展。二O二O年臺灣紀錄片《派娜娜》描述鄒族領袖高一生死於政治迫害後,女兒高菊花被監控、被脅迫性進貢。一群觀眾映後發言,不滿「電影打著高一生女兒的名號宣傳,為何不多著墨於高一生受害」。
同年劇情片《無聲》宣傳取材「發生在臺灣的真實故事」、「台版《鎔爐》」,報導文學《沉默:臺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的讀者指責劇情迴避、竄改事實,劇組則強調有虛構的自由。一些作者即使踩進各界政治黑幕,仍以「人性觀照」繞過雷區,深信一涉政治,藝術就死亡,淪為教條或宣傳。其實立場並未脫離政治,而身屬保守陣營。

本書日本記者沒有追問「這種文化差異是怎麼形成的」,如果抱持《殺人一舉》看印尼的角度來看臺灣,我想告訴本書的日本記者,2013年齊柏林導演的紀錄片《看見臺灣》空拍濫伐、亞泥天坑、高雄半導體大廠日月光排廢污染後勁溪、清境農場民宿如旅鼠大軍擁擠於峻嶺危崖之上,上映時因為配音旁白只歌頌美景、遇到醜陋真相就噤聲,而被罵爆;今天看來卻是臺灣極少數敢正面揭發權力黑幕的紀錄片。問題無人解決,甚至無下一部紀錄片深入現場。人們想的可能是如何再拍下一部票房2.2億的電影。
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系列報導之八〈從他們的眼睛看TIDF——訪TIDF外國影人吳文光、藤岡朝子〉中,「中國獨立紀錄片之父」吳文光導演說,2010年出任該影展臺灣競賽評審,看了十多部臺灣紀錄片,鮮少讓他眼睛一亮,有個性、有作者性的。大部分光鮮亮麗、講究技術,適合戲院、電影台播出。像在鏡頭前蒙了一層柔光紙,固然柔美,生動的東西到哪去了呢?跟他最初看到的臺灣紀錄片不太一樣,轉變讓他印象深刻。
生動的東西到哪去了呢?2004年《生命》票房3千萬,2005年《無米樂》票房854萬、《翻滾吧!男孩》票房518萬,2011年《翻滾吧!阿信》成本3千萬,賣破8千萬。紀錄片中身世悲苦又堅強樂觀的模範庶民身影創下高票房,企業從中找到了投資金雞母。拍片資金來了,留給那些像報導詹雅雯病情一樣的溫馨勵志故事,告訴受苦的人不要抱怨,要知足常樂,珍惜眼前,心轉境就轉。2007年《水蜜桃阿嬤》歌頌尖石鄉泰崗部落婦人艱苦獨養七名孫子女,因為二女婿、小兒子與媳婦都自殺。片末打出募款帳號,觀眾熱淚盈眶捐款,不會想到原住民的高自殺率與政策有關。喪事喜辦成潮流,企業投資拍片,紀錄片也變成假公益真圈錢的催淚廣告片。
2011年余光中傳記紀錄片《逍遙遊》避開他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的極權鷹犬角色,傲然視避重就輕為勇氣與堅持。西方紀錄片可以巡迴放映、有國內外電視台固定播出;吳文光說該屆臺灣紀錄片「適合院線、電影台播出」,道出臺灣除公視、國家地理頻道外,電視台不拍紀錄片,紀錄片遭院線高門檻生存挑戰下採取的捷徑:光鮮亮麗,柔美討喜。
網路上,林木材〈專訪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東京事務局局長藤岡朝子〉一文中,藤岡朝子說,歐洲電影有公共資金、電視台的資金、穩定的生活,即便團隊沒工作也很容易過活。但在亞洲,她更關心拍一部電影會遇到什麼困難,像是政治的情勢。
許多紀錄片都像《殺人一舉》中的農場工人畏懼安華勢力;甚至比工人更迷戀有安華庇護的安全感,而靠攏安華。相較於臺灣長期製造作者政治恐懼的利益集團從未現身鏡頭前,安華在鏡頭前自述殺人往事,單純得不可思議。你無法想像拍到顏清標、蕭景田自述犯案,甚至無法想像有紀錄片願意去傷這個腦筋。
書中,泰國導演阿比查邦說,泰國資訊受嚴密控制,任何書刊禁提法政大學大屠殺,「無法告訴大家發生在那個年代真實的事,就是現在獨裁者穩坐大位的理由之一。」
在臺灣,戒嚴時期形成的藝文體制仍牢牢控制著言論。既無紀錄片產業,也保障了權力不受挑戰。
有些紀錄片像一把石灰,倒進名為社會的那杯靜水,頓時便冒泡滾炸、翻天覆地。在視王力宏、徐熙媛婚姻為最大新聞、流量暴政所塑造的社會,這本書提醒觀眾,世界上仍有那些紀錄片存在。
我們的現況也許數十年後都不會改變,但至少要用病識感去過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