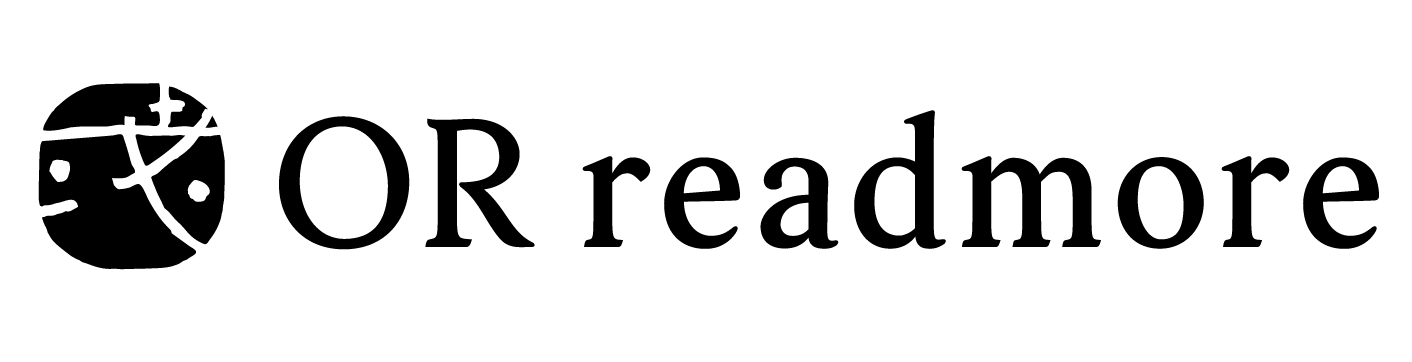炸物,或許是每個人的童年記憶中最富儀式感的食物了。將肉與根莖類切成各種形狀、大小,或裹粉上漿,或以原貌丟進滾燙的油鍋乾炸,等待外皮變酥脆金黃便可起鍋,清脆的聲響、香氣和溫度,刺激著人的所有感官。
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油炸作為一料理方式,就像是魔法般讓平凡無奇的食材轉變為美味誘人的佳餚,甚至被賦予奢侈、慶典、豐饒的象徵。曾經,酥脆的炸物只在年節婚慶等等重大場合才會被端上餐桌,孩子總是仰望垂涎這難得的美味。就算長大成人、經濟無虞,許多人仍然保留這那份對於炸物的情感記憶。
炸物這種曖昧的地位,引起了我的興趣。
對於出生於1990年後的我而言,最具代表性的炸物便是麥當勞,它充斥於成長過程中各個大大小小的重要時刻。在那個對於攝取熱量毫不忌諱的年紀,只要同學生日,必定選在麥當勞派對;段考成績出爐理想,也能得到一份快樂兒童餐作為獎勵。薯條、炸雞、可樂、漢堡,幾乎與童年裡任何值得歡慶的事有關。
年紀漸長後不只是麥當勞,街頭巷尾的雞排攤,作為便當主菜的炸豬排、炸魚排,到任何餐廳中五花八門的炸物都成了一種享受,一口咬下不僅為了攝取熱量,也滿足了口腹之欲的放縱。
如果我們將時光稍微回推,不難發現炸物被賦予如此特別的象徵意義並非偶然。將簡單的食材裹粉、油炸,並不如今時表面看去如此單純,在麥當勞與肯德基還沒出現的年代,菜糋與炸粿就已經存在於新竹人的生活與記憶之中。
位於新竹北門街尾長和宮旁的北門炸粿是新竹的炸物名店,相關的報導和食記多不勝數,都給了這間屹立不倒的小舖古早味的美稱。
這間大家口中的國民小吃雖然親民,且多年不曾漲價,但在過去其實是略顯奢侈的小吃。在物質匱乏的年代不僅吃肉難得,大鍋油炸更是非必要的消耗。對於當時新竹最為繁榮的北門大街來說,家家戶戶皆是商鋪,生活相對寬裕,一盤蚵嗲肉嗲是生活中的小確幸,但對其他百姓而言,這是在年節祭祀等等場合才有機會吃上一口的美味。
北門炸粿創立於日治時期,以肉嗲、蚵嗲、蒜苗最為著名,炸物外頭的粉漿以在來米為原料,與今日常見的麵粉炸物極為不同,較接近日式天婦羅的做法。
相較於炸粿的市井氣息,菜糋更親近農村常民,以根莖類作為主要食材,裹粉也因地制宜。菜糋的食材雖不稀有,但仍是生活裡的奢侈品,要起一大鍋的油製作食物,仍非日常所能經驗的事。菜糋,雖然稱不上特殊的美味,在許多人的家庭記憶中也不陌生,但只要談起這道料理,稍有年紀的長輩們都有滿滿的美好回憶,與之相伴的不外乎是母親獨特的手藝與年節時的熱鬧場景。
在以農為主的年代,菜糋的食材大多就是自家菜地的作物,不外乎地瓜、芋頭、花生等等製作。只要將這些根莖蔬菜簡單切片、裹上粉漿,下入油鍋酥炸,這些平凡的材料就彷彿被賦予了新生命,成為大人小孩愛不釋手的佳餚。
這道料理出現的關鍵之一,在於麵粉。雖然早在美援之前,麵粉就已經出現於台灣的料理之中,但使用並不普及,而美援中的大量麵粉除了促成了麵包、麵食的興起,也悄悄走進了更多尋常人家的廚房。
菜糋,便是將家庭農產裹以粉漿麵衣所製作的料理,食材隨著風土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常見的有高麗菜丸糋、芹菜糋、南瓜糋,在澎湖更有海鮮糋,新竹南門地區因為閩客交界處,則以自家生產的花生混上客家人所賣的酸菜,製作出帶著酸甜滋味的酸菜土豆糋。

「小時候家裡窮,沒什麼好吃的,菜糋便是最美味的零嘴」鄭主竹說。
這天我們跟著鄭主竹訪問他的母親,詢問菜糋的製作方法,打算找個時間再來重溫母親的手藝。
菜糋是家庭祭祖時最重要的食物之一,前一天晚上就必須開始備料,以便隔天一早快速下鍋油炸,並於此同時也準備其他祭祀用的菜餚。對於小孩而言,幫忙準備的同時也有機會偷吃一口剛起鍋的菜糋,那時炸物最美味的一刻。
製作當天,兄弟姊妹難得在疫情緩和之時齊聚一堂。花生油的香味,讓眾人想起小時候的生活,夾起一口菜糋,每個人都有說不完的故事。
同樣是炸物,如果說北門炸粿帶領我們看見新竹舊城區商業街熱鬧的景象,菜糋則是代表著城外農家的傳統生活方式。
對於物資無虞的現代人而言,抱著對熱量和致癌物質的隱憂,人們往往有意識地計算攝取了多少炸物,飽餐一頓後便伴隨濃濃的罪惡感,炸物成為繁忙工作後犒賞自己的獎品。
從古早味炸物、美式炸雞到四處可見的雞排店,當粿粉覆蓋住食物原初的模樣,油炸作為一場儀式,它化生為熟、化簡為繁,成為人們對於節慶、祭祀的想像延伸。
就算暫且不談油炸如何鎖住食物的美味,炸物的儀式性或多或少來自於它作為非日常飲食的特質,在不同時代內蘊著不同張力,永遠保持著新奇感。
差別僅在於,過去的炸物必須跨過物質的門檻,現在,人們警惕的是它所蘊藏的熱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