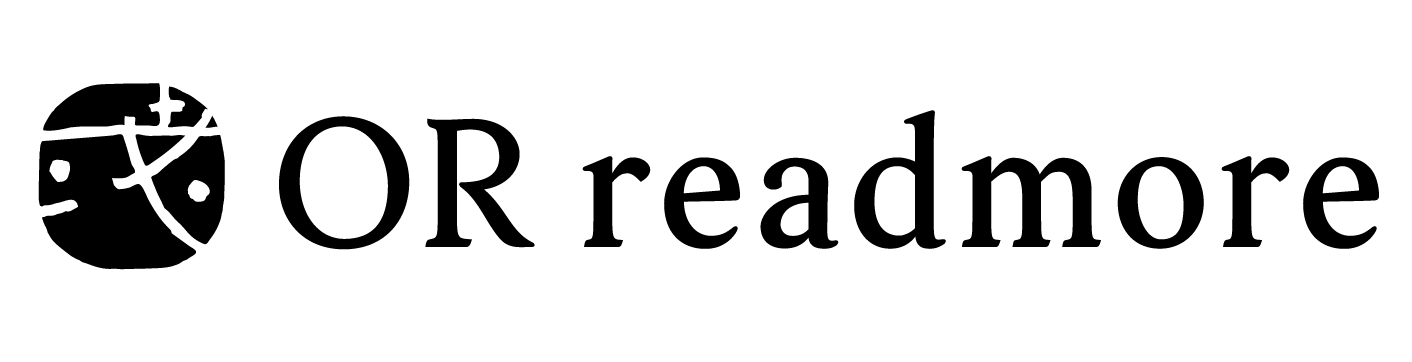九月和朋友們去屏東好茶玩。穿過前廊,在魯凱族百合花、十字架環繞的私廚飯廳裡,沿窗掛著成串黯紅纍垂的紅藜長穗,白牆相框裡一張張小照,這張是主廚母親國中時,在舊好茶部落石板屋前留影的黑白照片。那張是成年後的特寫,短髮深邃大眼,純真堅毅的短方臉,眼神豪邁不羈。一張少婦時背著抱著兒女涉急流過溪的照片。像是坐在一本打開的家族相簿裡,我們在逝者殷勤的注視下,吃她兒子用月桃葉捲裹的烤山豬肉、橄欖油烤蔬菜、錫箔紙小杯裝的小米布丁,對每道菜大讚好吃。中年主廚只在上菜時介紹了菜色,就退回廚房,全程沒多說什麼,而我們卻像是來弔祭故人般滿懷溫情。想著時髦的烹調和裝盤底下,是否藏著母親調味的靈魂。
這是星期三的夜晚,飽飯後在部落街道散步,發現近處有教堂。整條街家家戶戶都暗了,只有門裡滿堂光亮,原來人都在這,長椅坐滿了人,講道、讀經。門口三個七、八歲的小男孩小女孩,在台階上自己玩,好奇張望來人。朋友們像平日在幼稚園跟孩子同學交談那樣,跟小孩搭話聊了起來。對門家屋也是暗的,一條大黑狗從趴著的門前擦鞋墊起身上前,過街慢吞吞來到我腳邊,嗅聞我褲腳。我把手伸給牠,像平日搭話那樣聊了起來。
黑狗在黑夜裡顯得龐然大物,面貌不明。抓抓牠的後腦勺,牠便趴倒在路中央任人伺候,如同廟會大豬公。我手指頭跟牠唏唏嗦嗦地扯著廢話,要從牠的耳後搔抓到肩膀、到腳呢,足足可以花上一個鐘頭。手裡捉摸著牠粗短的硬毛,聞著那狗味,心情愉快極了。直到背後朋友喊我「我們要走了」,我才回神,慢慢站起來。
小孩們回到教堂門口,而狗跟了過來,陪我們在芒草飄搖的秋夜裡一路逛完半個聚落。然後在通往所投宿民宿的路口,牠像是比我還先明白夜遊告終,「那我走了喔」掉頭而去。
民宿的規矩是,住客要把鞋子脫在柏油路邊,才踏上前院的磨石子地板。闊大的前院裡,擺了幾條太師長椅,是日常聚會的客廳。進門的客廳反而侷促,樓梯邊堆滿了紙箱,標籤印著貨品名稱「罐裝紅藜牛軋糖」,一旁沙發茶几半掩在黑暗中,光裸沒有椅墊、提包、外套、遙控器之類雜物,看起來沒人使用過。
星期四,鳥啼聲中天剛亮,照例要去山林裡晃蕩,起床發現球鞋不見了。我回頭進客廳,民宿李老闆的媽媽剛從廚房幽暗中鑽進客廳,母子住在後棟。她聞言驚訝,忙帶我出門,在坡道上說,你找這邊,我找這邊,就看有沒有在別人屋前草叢裡。我借了一雙螢光珍珠粉紅、亮面浮凸顆粒的塑膠拖鞋去滿山張望,走了二十公里,把部落裡外都刺探了一番。然後細雨中在陡坡上滑了一跤。一屁股泥濘。
李媽媽沒有找到,我也沒有。我天天穿便宜球鞋、穿壞才換,而那卻是我買過最貴的球鞋。因為在東京旅行時,鞋底脫落了,所以在百貨前廣場的特賣會,臨時買了半價六千日圓的耐吉鐵黑織紋球鞋穿回來。為的是想知道貴一點的鞋是否造得更牢靠、不容易穿壞,結果現在等不到答案了。回想起來總覺得窮人一花錢就沒好事,好像是因為不安分守己,做錯了事所以受懲罰。
我走山走累了,回民宿鑽進被窩睡了一會。醒來出房門,朋友轉告我,李媽媽說,她找得很辛苦,可是沒找到,民宿老闆會給我人字拖應急。我腦袋空空地說「喔」,知道該去謝謝李媽媽找鞋的辛苦,不該把這種事放在心上打擾遊興。但現在要我體諒別人,就像直接打我一巴掌叫我守規矩一點。
我想要把自己封進一個罐頭裡,可是我找不到那個罐頭。
部落的人們說「很少發生這種事」,我覺得好像在怪我不該發生這種事。對我要求廣播協尋,他們報以沉默,或詫異失笑。我感到在異世界語言不通、迷路回不了家那種熟悉的絕望。
近午下了山,從計程車的車窗望出去,路口淹了大水,司機說這路段常常淹水。車子就從水裡穿過,像是陰陽兩隔。
回到台北,結果雨下得比南部還大。

離開好茶的頭兩天,連續收到兩通未接來電。一看,市話區域碼屏東縣,我頓時燃起希望,覺得民宿李媽媽要告訴我,鄰居路過發現鞋子躺在草叢中,拿來給民宿。
可是,每次我回電,都沒人接。聽著每一響嘟嘟聲,知道電話同時在民宿客廳裡空響。心想著,這時民宿裡,李媽媽在忙碌接待住客,吩咐兒子開車下山採購記得買衛生紙、清潔劑、洗衣精,那麼米也沒有了。去園子裡摘野菜,去別人家幫忙生孩子,幫忙捏飯糰慶祝,去別人家聊天唱歌,去出貨,去教會,送老人下山去看病。
不知不覺,我偷偷在參與她的生活,看她什麼時候回過頭來發現我在等她。
聽著電話嘟嘟響時,我每天有了幾分鐘待在部落,待在沒有人的客廳裡,沒開燈,跟躺在瓷磚地上像張床般矮闊的冰涼棕紅大沙發、茶几,跟一堆罐裝紅藜牛軋糖紙箱、住客的行李箱在一起。我看著廚房的門,也許李媽媽會從那幽暗中悄悄進來,像我待在那最後一天早上那樣。
我電話打了好幾天,有次有人接了。是年輕女孩,說她是民宿客服,但是負責鞋子的窗口此時不在,那個窗口會再回我電話。
下次是我週日晚看完電影開手機,發現漏接一個手機號碼。此心不息,我又愚勇幻想鞋子回到我身邊,和好如初。打去,對方是菸酒嗓鼻音濁重的男人,說打錯了。我說好,謝謝你告訴我。對方委屈可憐地說,眼睛不好,看錯了。我嚇一跳,眼前浮現那白內障渾濁油膜淡藍的眼瞳。那人生苦難無奈,遠遠多過打錯電話、滲了過來。趕忙安慰他,說謝謝。
但這個號碼又出現了好多次,每次接到,都說打錯了。
他可能是那個被推舉、被期待要來告訴我什麼的人,只是臨場退縮了。他作為勇者,艱苦卓絕,一次又一次挑戰了大魔王的我,卻跨不過羞怯本性,棄甲而逃。那麼,到底還是一個壞消息。我想著她們吃飯時圍在一起開會,為了誰去傳遞壞消息而苦惱的場面。那句話難說的程度超乎我的想像,到底我給他們造成了多大的壓力呢。
有一次我回撥,女孩終於告訴我,他們有繼續找鞋,但沒找到。在我想像中,那個濃眉大眼的漂亮胖女孩,垂下眼角,低聲安撫。聽她說著:「對不起啊。」我答:「沒關係啦,謝謝你。」「真的很對不起啊。」「謝謝你。」「對不起啊。」「謝謝你。」像是兩個老友在搶餐費帳單,或是推讓一份名貴禮物,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夠的纏綿二重唱。
感覺我似乎走進她家住了一個月,像是客廳角落裡棲宿的鬼魂,跟這家裡的人、打工的每個人打過交道。而其實我跟誰都不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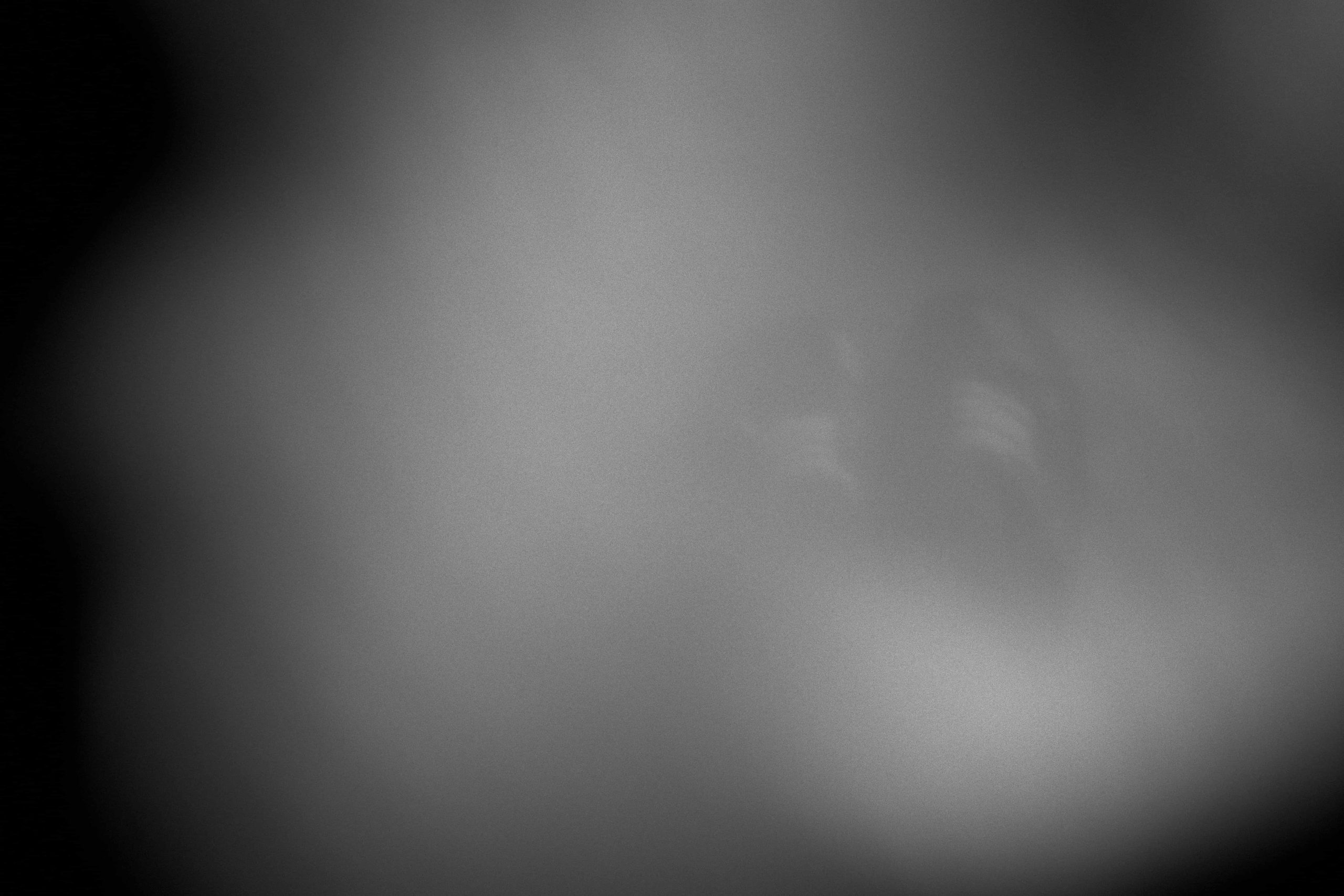
這一個月間,台北傾盆大雨,我等著我的鞋回來,不買新鞋。可以說,我處於否認期。
出門就穿拖鞋,可是下雨會滑。姑姑給我一雙去美國旅行時買的名牌皮面氣墊球鞋,放了幾年沒穿。中午我穿上出門,發覺鞋子很緊,好處似乎是防水膠底,襪子不會濕透。後來發現,是因為太緊了,蹭得難受,所以濕了也不知道。就像是有人態度太嚴厲,那麼就算是他口臭,你也不會注意。因為他的態度就讓人想逃,沒人會進入口臭半徑,所以口臭根本不是問題。
因為太久沒人穿,鞋底遇雨,幾小時以後,先是從鞋尖稍微鬆脫。接著滾雪球越塌越大,一半鞋底都分了家。
回家後,我把鞋子拿去陽台晾乾。這才發現手機關了靜音,剛才又未接屏東電話號碼。如獲至寶的我跳起來秒回撥,問鞋子是不是有消息了。簡直就是尋母三千里。
結果是民宿李媽媽。她告訴我,找得很辛苦,可是沒找到。
我驚訝得說不出話,最後還是loop反覆謝謝她,收線。想到這一個禮拜,我每次回撥,或許都有人在晚飯時傳話告訴她,有人在問。所以她想著要告訴我沒找到。
她一次一次的打,就想說一聲。要告訴我沒找到。難說的話,還是要說。頓時我的心變得又濕又暖。那些未接顯示,好像住教會對門那頭肥胖黑狗打了很多電話給我一樣,使人欲淚。
去屏東以前我暗暗覺得民宿好貴,國內外背包旅館,上下鋪幾百台幣待一晚比較輕鬆。而此刻我像著了魔,雖然即使見了面都說不出什麼,卻想著我要再去她民宿住一趟。為了證明我此刻的心意,我覺得我得去看她才行。
落單的球鞋,裹著透明塑膠袋,像個屍袋,躺在床邊。我看著那隻鞋,像見到掃過樹下、初秋的晚風裡,那黑狗枕在我的鞋子上,看著群山逐漸暗下來,一天又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