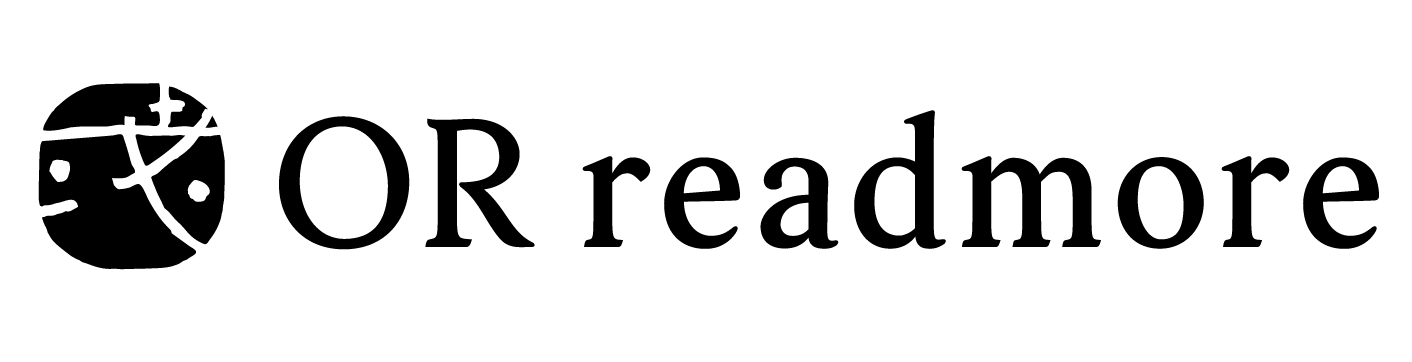因緣際會,透過友人協助而邀請作者平路蒞臨月讀,和我們聊一聊新舊故事之間,那些斷裂與連結,重整生命,說出那些非說不可的事。
許多讀者都是平路的資深粉絲,從三十幾年前發表《玉米田之死》到《袒露的心》,有讀者說這三十幾年來看著平路的文字獲得紓解與療癒;有讀者說每次聽平路談及寫作,都很認同那股認識自我與面對決離的心境,那是年近中年才能體會的釋然;而在場的讀者也很想知道,平路究竟是從何時開始以創作做為認識自我之路?
平路笑道這是一個好問題,事實上許多問題都是成了問題之後才能進入思考。當時的她在美國念了博士班,論文沒完成,先找到了工作,並且是數理統計專業的職務,旁人看來事業上可說是一帆風順,然而她的抽屜裡總是有著尚未成形的故事,紙筆中有著對當時的她而言非說不可的故事。
故事中的結尾,成了她人生的預言/寓言,一路寫著寫著,原本正職的工作自願轉為兼職,又過了幾年再轉成全職寫作,究竟是寫作找到了自己?抑或是自己選擇了寫作?這倒也很難說得簡單,但成為小說家,的確是人生規畫以外的事。

期間曾關注淡水媽媽嘴咖啡店事件,或許跟自己過去從事報業、任職新聞中心的職業有關,看見八卦雜誌沸沸揚揚以一種睥睨的高度評論著事件發生的所有關係者,以非黑即白的貼標方式區分了那些蛇蠍女、惡人與我們。
平路認為小說家同樣關注、卻希望以齊平的視角觀察著與「我們」,我們並無異於他人,我們可能會是殺人者,也可能成為被害者,而為什麼沒有跨越那一條線,這是身為小說家所關注的視角。
當《黑水》出版不久後,媽媽嘴咖啡店負責人呂炳宏私訊了平路,說他一口氣讀完,很震驚這位與他們完全沒有任何接觸的作家,為何能夠寫出這麼貼近他所認知的事實。事實是,他認為最可怕的不是犯了殺人罪的店長,而是鄰人的耳語與跟著風向走的輿論,這些以種種早就覺得有異的閒言閒語,才是真正的惡。
從社會事件聊到自己,平路意識到寫作是一種跟童年經驗的斷裂或連結,《袒露的心》花了好幾年功夫完成,卻在出版在即,揪結著乾脆別出版了,這些這麼袒露自我生命的故事。
從以為自己的獨特性為始,而以自己並不獨特作結,是創作時的歷程。
梳理自身的生命,一步步才能看見自己並不特殊,任何際遇、苦難、悲痛與遺憾,都不是唯我獨有,而自我與他人之間的距離,各種理解的距離,包括安全的距離、願望的距離、幸福的距離、乃至婚姻的距離,有時候最熟悉的陌生人莫過於枕邊人了。
“當理解這個距離有多少差距時,更不能忘記:每個人都是遙遠的國度,要探索他(她)的心,要先在峭壁之間闢出良港。“ - D. M. Thomas《白色旅店》
人與人之間的細絮蛛網,藕斷絲連,這些經驗的探索或許是洞察、或許是修復,這些關係之間,曾後悔自責、或壓得自己喘不過氣,這些抉擇與承擔、沉重與罪責,可能都不是被原諒所能救贖,原諒自己並且接受自己,當下即豁達。
當人們問達賴尊者有沒有後悔的事情,人們期待的是超越凡人的答案,而達賴尊者說自己和別人沒有兩樣的後悔與遺憾,但是不能被這些事情所拖著,並非否認這些情感,而是不被拖著動彈不得,生命才得以繼續。這樣的回答,回到人間,回到體認,闢出良港,承接住自己與他人,生命課題的答案,也是宇宙的餽贈。
(新舊故事之間——文字所聯繫起來的|平路分享會 10/19 (六) 14:00-16:00)